落得一个客死蛮荒之地下场的原因是什么-北宋名臣寇准 (落得一个客死的成语)
力挽狂澜、避免北宋提前变成南宋的寇准,为什么会客死蛮荒之地?是很多人要的问题?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答,国封建历史上有个奇特的规律,那些在政权生死存亡之际,挺身而出、挽狂澜于既倒的能臣,大多...
力挽狂澜、让北宋没提前变成南宋的寇准,最后怎么就客死蛮荒之地了?这问题估计不少人好奇吧,今天就来唠唠。
封建历史上有个挺怪的规律:但凡政权快不行了,能站出来力挽狂澜的能臣,最后大多没好下场,比如北宋的寇准、明朝的于谦,都挺惨的。
就说寇准吧,当年辽国刚打赢几场仗,仗着势头猛来打宋朝,朝里一堆人喊着要往南跑。寇准偏不,硬是劝动了宋真宗御驾亲征,靠着那股子狠劲儿和正确的打法,把局面给掰回来了。要不是他,北宋变南宋的事儿,估计得提前一百年上演。
可这么个国之栋梁,后来却被一贬再贬,最后孤零零死在蛮荒之地。好在宋朝还算给文官留了点面子,换别的朝代,寇准估计早就人头落地了。
那寇准为啥落得这个下场?跟于谦一样纯粹是被小人害的?倒也不全是。有句挺俗但挺实在的话,能解释他的遭遇:性格决定命运。
有人说“北宋没血性”,这话有点冤。刚建国那会儿,赵家皇帝们可没少想夺回幽云十六州,只可惜实力不济。
979年,宋太宗打完北汉,没喘口气就转头打辽,想趁辽国不备拿下幽州。开头还行,好几个辽国守将投降;可后来辽景宗派精骑反扑,宋军三面受敌,被打得稀里哗啦,死了一万多人,宋太宗自己坐着驴车狼狈逃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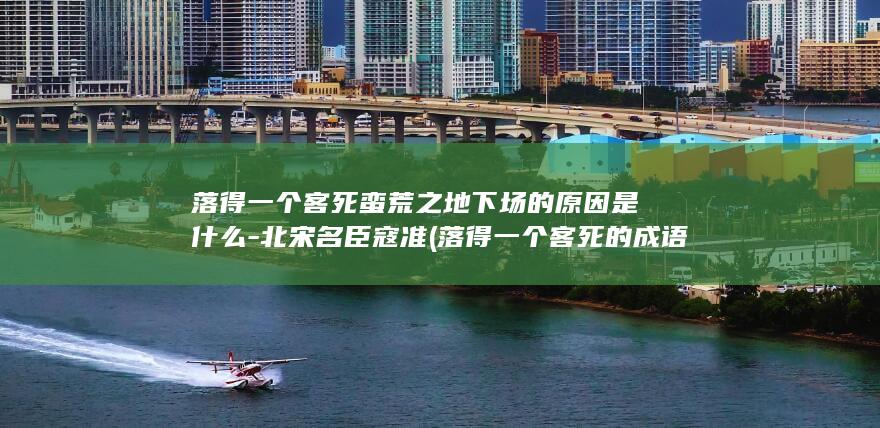
这一战算是把宋军高歌猛进的势头给打断了。但宋朝可没死心。982年,辽景宗死了,宋太宗琢磨着辽圣宗年幼、政局不稳,又想打幽州。结果呢?撞上了萧太后带着圣宗亲自督战,在岐沟关把宋军打得大败。接着辽军全线反击,潘美败了,杨业被擒,蔚州、寰州这些地儿也丢了。
这一仗北宋亏大了,不仅没拿到一寸地,反而丢了地、花了钱、死了人。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军队那股子锐气,这下彻底没了,北方边境的仗,主动权全落到契丹人手里了。
自打这以后,宋军精锐没了,士气也低落,朝廷里怕辽的人越来越多。辽军呢,趁机从守转攻。986年,辽军南下,耶律休哥打瀛州,宋军在君子馆被打得大败,死伤好几万。接下来的三年,辽军一路高歌猛进,深州、祁州、涿州都拿下了,甚至打到了青、淄、齐、潍十多个州。契丹骑兵到哪儿,百姓就被杀,财富就被抢,房子被烧,北方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到了1004年,萧太后更狠,带着辽圣宗御驾亲征,带了20万人,这架势明显是想一举把宋朝给灭了。
不过这时候北宋掌权的是寇准。跟后来宋朝那些文弱宰相不一样,他有点“非主流”:不仅懂军事,胆子大,战略眼光也好。早些年辽国在战场上占便宜,寇准就琢磨着,他们野心肯定越来越大,肯定会更激进地打宋朝,所以早就让人“练师命将,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”,各方面都准备好了。
所以辽国大军一来,朝野上下慌得不行,寇准却跟没事人似的,一天五封边境告急文书,他照样“饮笑自如”,跟定海神针似的。
果然,开头辽军好几路一起打,没达到“摧枯拉朽、所到即破”的效果,打威虏军、顺安军这些地方时反而老吃亏。后来他们打下祁州,合兵一路往南,杀到澶州(今河南濮阳),把这座中原重镇给三面包围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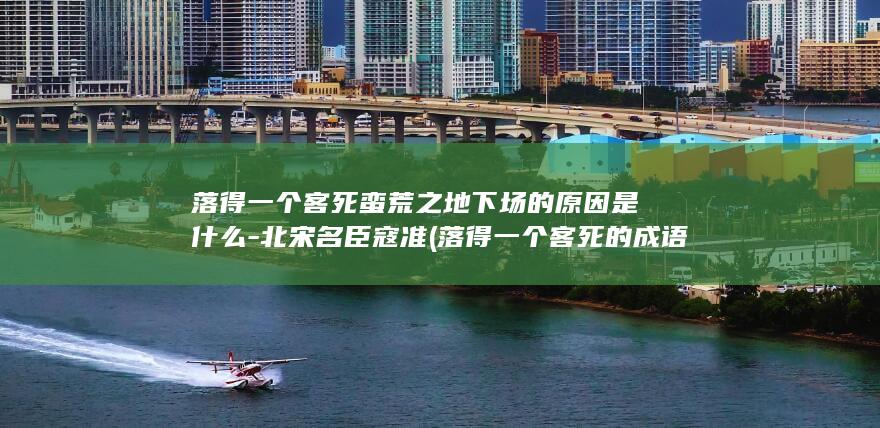
等“契丹围瀛州,直犯贝、魏”的消息传到开封,整个朝廷都吓蒙了,投降派们吵吵着要学司马氏南迁金陵,或者学李隆基跑巴蜀,七嘴八舌的,宋真宗也拿不定主意,只能去问寇准。
寇准早把局势琢磨透了,他觉得敌军远道而来,不可能一直这么猛;宋军虽然形势不好,但打起来有股子劲儿,要是“坚守以老其师”,赢面不小。反过来要是朝廷慌着跑南边,人心一散,敌人趁机打进来,大宋半壁江山就没了。最后宋真宗被说动了,带着文武百官御驾北上。
可到了澶渊边上,大家都怕契丹的威风,主张隔着黄河给宋军打气,宋真宗自己也差点退缩。但寇准和高琼非让他渡河,还登上澶州北城门楼督战。
皇帝一到前线,宋军士气立马起来了,契丹人猝不及防:“远近望见御盖,踊跃欢呼,声闻数十里。契丹相视惊愕,不能成列”。澶州附近大宋军民几十万,胜利的天平慢慢往北宋这边倒了。
接着寇准拿到前线指挥权,他“承制专决、号令明肃”,士兵们高兴,宋军越打越勇,没多久射死了辽军大将萧挞览。辽军士气垮了,萧太后他们哭得不行,“辍朝五日”。没多久,进退两难的契丹人主动求和。寇准本来想趁势逼辽国退幽州,但宋真宗急着和谈,最后签了“澶渊之盟”,宋朝从此有了差不多一百年的和平。
寇准在这次危机中的作用,跟明代北京保卫战的于谦有点像,都是在危急时刻力排众议主张硬刚,最后扭转局面。但和于谦不一样的是,澶渊之战还没打完,宋真宗已经开始怀疑寇准了。
宋真宗为啥占着便宜还急着和辽国谈?厌战是一方面,更主要的是朝里传寇准想“拥兵自重”,这话可戳中了皇帝心里最怕的点。面对“准幸兵以自取重”的谣言,寇准也没法坚持,只好顺了宋真宗的意思,但他还是争取了,把北宋的议和成本压低了不少。
澶州保卫战,北宋虽然没打赢辽国,但彻底扭转了之前被动挨打的局面。“河北罢兵,准之力也”,寇准作为头号功臣,这时候也到了他事业的顶峰。
可人性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毛病:危难的时候,我们欢迎、渴求英雄;可危机一过,立马忘了人家的功劳,反倒盯着人家的成功和声望嫉妒、仇视。这就是“大名不可久荷,大功不可久任,大权不可久执,大威不可久居”背后的道理。
所以有些能臣立下大功后,会刻意收敛,甚至急流勇退,比如再造大唐的郭子仪。但大部分人还是被各方猜忌、排挤,没好下场。人性丑恶当然是主因,但当事人自己也有责任,比如寇准。
寇准性格强硬,本来就瞧不上官场那套弯弯绕。平时“用人不以次,同列颇不悦”,提拔官员不按资历,凭自己喜好来,早就惹得大家不满。战后成了英雄,声望一天比一天高,宋真宗表面上对他感恩戴德,越来越重用他。寇准却没意识到危险,还挺得意“准颇自矜澶渊之功”,这就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点。
比如王钦若就说“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”,把这场战略成功说成耻辱。寇准把这当成自己的功劳,等于拿皇帝、朝廷的尊严给自己贴金。宋真宗一看,“顾准浸衰”,第二年就把他宰相免了,降成刑部尚书。这时候这些人可能早忘了,当初没寇准,契丹人不可能低头和谈;更别说,澶渊之盟还是他们自己坚持要签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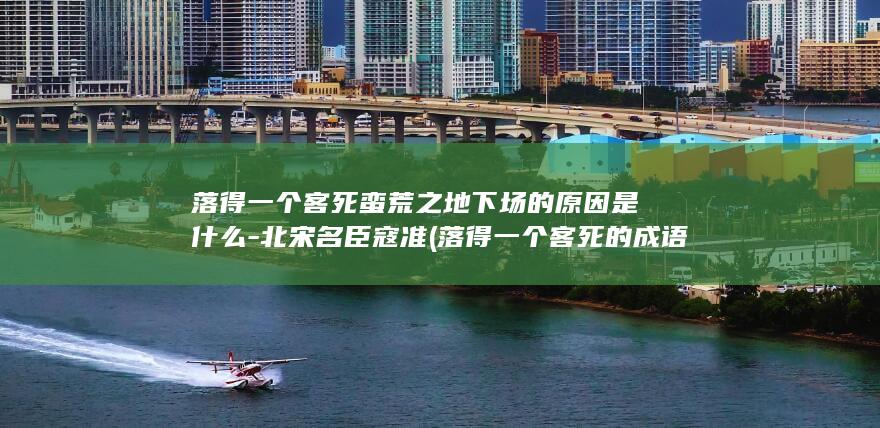
除了功劳被嫉妒,局势稳定后,寇准的性格缺点也慢慢显出来,无形中让那些心里有气的同僚找到了攻击点。比如他疾恶如仇,对普通人来说是优点,但在关系复杂、利益纠葛的官场里,这种性格不仅解决不了问题,反而会招更多敌人。加上他气量小、太专权、争强好胜,慢慢成了众矢之的。
他曾跟张逊互相弹劾,结果被罢官去了邓州;后来又官复原职,却因为点小事得罪了丁谓,掉进对方处心积虑的坑里,再次被贬,赶出了京城。
宋真宗其实一直不太想用寇准当宰相,理由是“患其刚直难独任”。说实话,这担心不是没道理,宰相这位置太重要了,能办事是一方面,能协调各方关系、调动大家积极性才更关键。寇准确实有才,但性格实在不适合当宰相,甚至待在朝廷中枢都难。这就是现实。
后来丁谓大权在握,对寇准一贬再贬。曾经力挽狂澜、救了大宋的功臣,就这么没善终。这本质上是封建政治的悲剧,有政敌小人使坏的原因,也有宋真宗自己的考虑——皇权向来怕相权,何况这皇帝本身就犹豫多疑。在这种复杂局面下,寇准自己的性格缺点,更是把自己往坑里推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