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语录摘选鉴赏-有关于銮披汶·颂堪的评价有哪些 (人物语段摘抄)
民主试验时期国际访问1955年4月至6月,披汶·颂堪访问欧美回国后带着一种对民主的热情回到泰国,他的公开资态,几乎与美国新选出的主张改革的执政者没有区别,大部分观察家把这种转变解释为企图争取人民支持,...
民主试验时期
国际访问
1955年4月到6月,披汶·颂堪跑了一趟欧美,回来后突然对民主来了劲,态度跟美国刚上台的那些主张改革的政治家似的。当时不少观察家觉得,这转变八成是他想拉拢民心,好重新掌握1951年政变时丢掉的权力。按他们的说法,披汶在美国、欧洲和亚洲几个国家转了一圈,发现真正民意能让一个国家领袖拿到多大的政治权力——要是艾森豪威尔那套“仁慈”手段,比佛朗哥的镇压更能换来政治安全和国际威望,那为什么不试试呢?这些观察家还注意到,这是披汶自2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国。不管这总理为啥突然想当“民主派”,反正他这一套,民族主义的味儿淡了不少,毕竟之前的排华政策,多半是打着反红色中国的旗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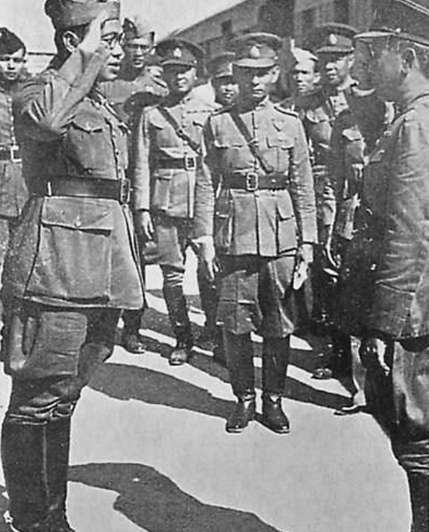
政体自由化
披汶自己其实挺悲观,觉得“民主意识在泰国扎根,怕是要等30年”。不过他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,开始折腾改革,非要让两极格局变成多元并立,哪怕搞得政治集团分裂也认了。他干脆放开言论,整个社会开始有点自由民主的意思了——学英国的“海德公园”,在曼谷搞了几个自由辩论中心,让大伙儿能随便集会,比如王家田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骂政府、抨击时弊的地方。政府还废了新闻审查,媒体啥都能说,连政府内政外交都能批。披汶自己也借机让媒体曝光政敌丑闻(他自己本来就清廉,抓不到把柄)。他这么干,一方面是想让国民多“自由民主”精神,另一方面也是用社会舆论压着沙立“陆军集团”、帕敖“警察帝国”瞎捞钱、乱扩权,还得防着“两极”动用政治暴力。开放党禁,降低投票门槛,他还带头组织政党参加1957年2月大选。1955年9月,国会通过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个《政党法》,政党能注册了,连左翼政党也能活动。披汶自己拉了个玛兰卡西自由党当核心。他还把合格选民的年龄降到20岁,取消文化水平限制。学欧美国家搞市政厅,还宣布:“公民有权利向政府发表自己的意见。”1956年又通过《选举法》,想加强国会权威。
内务与民生建设
披汶使劲推廉政和反腐,想把政治和钱分开,削弱沙立和帕敖的势力。他对财政货币政策动了大手术,取消多重汇率,搞统一的固定汇率,贸易也中立化了。基础设施他也没落下,还把那些跟基础设施无关的国企私有了。1955到1957年,美国经济援助多了,用来改良农业灌溉,修高速路、盖学校。1956年,他推动泰国史上第一个《工人法》,规定工人每周最多干48小时,工资有个最低标准,1957年1月1日直接关了1090家有执照的鸦片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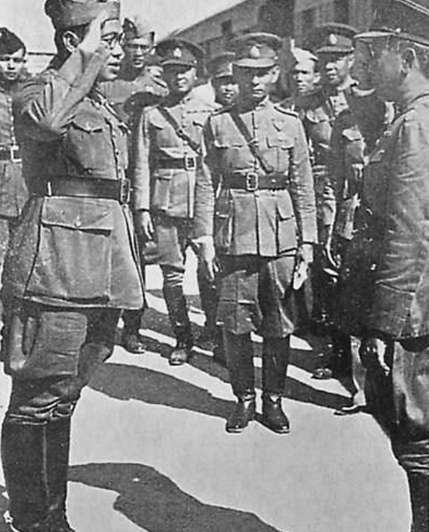
传媒
1950年8月21日,披汶向议会提了个无线电传真研究项目,1951年开始搞。1955年6月24日国庆日,他办了个仪式,庆祝政府主导的电视九台成立,宣布泰国电视办公室成立。后来电视广播被他用来搞国家建设和爱国主义宣传了。
外交中立化
1955年后,披汶的政策受“万隆会议”启发,整个氛围温和了不少,结果泰国周边国家左翼和右翼的平衡给打破了。比如老挝皇家政府,就因为泰国的立场动摇了反共决心。1955年12月,披汶访问缅甸,两国关系热络起来,1956年初缅甸的吴努也回访了曼谷。中立主义还让他撤回了对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支持。1955年12月,他派秘密访华团去了中国,算是中泰交往的第一步。1956年8月19日,泰国最高顾问乃讪(披汶支持他)通过绝密渠道,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共和国,大陆和泰国的关系开始缓和。虽然还没建交,但商业贸易正常起来了,两个政府的关系总算有点苗头。1956年夏天,披汶政府开始跟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波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贸易,还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。要是披汶政权能撑到六十年代,那时候的泰国政局肯定不会像后来那么压抑凝重。
披汶之得失
但看国际形势,50年代后期中南半岛正在重组,越南南北分治、老挝内战一触即发、马来亚和菲律宾有红色危机、缅甸又有社会主义思潮,美国人更看重泰国的稳定了。可这时候泰国因为披汶的“民主改革”,反而多元化了,左翼起来了,民族主义也冒头,披汶顺着民意慢慢放弃“亲美反共”,搞自主外交,跟美国利益对不上,美国不高兴了,开始在泰国找新的代理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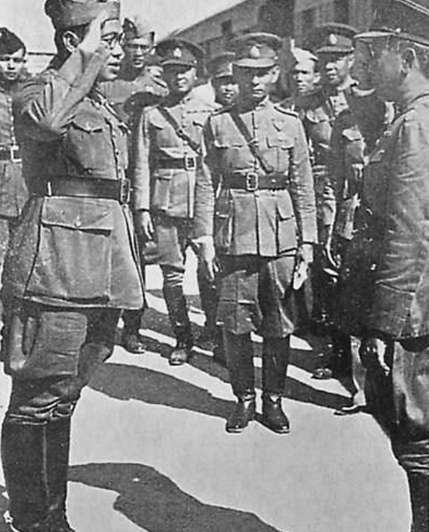
家庭
披汶这辈子唯一的妻子拉雅迪(1903-1984),是泰国妇女委员会创始人,当老师的她还帮着披汶搞女性教育、儿童福利、泰国医疗事业,是个女权主义者,1984年5月3日去世。儿子普拉颂·披汶颂堪海军少将,1951年后接手重组后的王牌海军陆战队。小儿子尼特·披汶颂堪(1941-2014),2006年当泰国驻美大使,2014年死于淋巴癌。
人物评价
中国人常说“盖棺定论”,但大人物们总是免不了被人拿来说嘴,披汶也一样。社会各界对他褒贬不一,有的泰国人说他民族英雄,有的说他锲而不舍、乾纲独断,像个帝王。华人激进点骂他是华人败类、美国走狗。欧美人倒是客观,叫他独裁者。到底该怎么看他,真挺费琢磨的。
比里·帕侬荣晚年回忆说,披汶相貌英俊,个人魅力爆棚,说话特有说服力,留法学生里人人都对他印象深。
披汶掌权十五年,争议一直没停过。一方面他热衷权力,对潜在挑战者反复无常,多半是姑息养奸,盲目仁慈,第二个任期弱到对炮、沙立的腐败扩张一点办法没有。另一方面二战时他维护了泰国独立,暂时挽回了民族荣耀,很多泰国老兵怀念那个时代。披汶政策上咄咄逼人,用个人魅力塑造了自己的时代。但可惜,第二个任期里,他在可能失去权力的斗争里变了,不再是40年代那个锋芒毕露、搞国家建设的领袖,成了个世故圆滑、内斗费劲的政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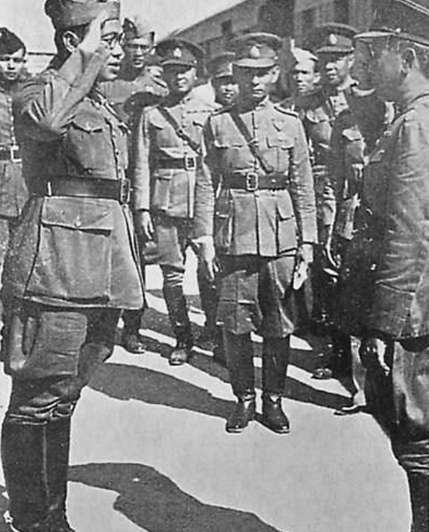
戴维·K·怀特亚评价披汶:他是泰国历史上少数能留下自己印记的人之一。他第一次上台从1938年底到1944年中期,那段时期完全靠他的权力和人格塑造,就像几十年前的专制君主一样。他的权势上升跟二战同步,政策跟泰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(比如他宣传的泛泰主义、普世价值观,还有推广的泰式炒河粉)。最重要的是,那是大众民族主义时代,不是精英民族主义,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比君主制下更接近平等主义。后来几十年泰国人说起第一个披汶时代,用“我们”的时候,表示的是对国家生活的公共参与,跟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。
披汶元帅对民主贡献挺大。但他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,基本人权被践踏得比专制时代还厉害。民众被迫接受新文化,被强迫穿衣服,女士得穿裙子……咱们的爷爷奶奶辈被强迫放弃嚼槟榔和其他传统习惯。
人物语录
爱国主义是受过良好教育者的基本美德,也是所有文明国家的基本要求。
就杀18个人,还能算多吗?法国大革命时砍下的头装车都能排成队。
如果我们对国家的热爱比不上其他国家,那么,我们的泰人国家就无从期望还能在国际社会中自由长存。
哪一方在战争中溃败,哪一方就就是我们的敌人。
国家与佛教不可分离。宗教是民族文化和道德的柱石,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繁荣与稳定。与此同时,唯有国家的稳定和统一,才能确保佛教的生存与发展。两者盛衰与共。
军队是国家之藩篱。
我不过来自农民家庭的平民,而不是神圣后裔。
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过渡条款的延期问题,我们就将不得不面对更为严重的难题……首先,那些(保皇派)海外流亡者必然会归国,并通过金钱铺路的方式进入国会;其次,外国人特别是华人在国内人数众多,如果选举,他们就有能力组建政府。……那么我们将失去对国家的统治权,我们将无法在泰国继续生存。我们必须时刻确保手中的政治权力。否则,我们必将走向毁灭……(政府内阁会议备忘录,18/2483,1940年7月24日)
如果不尽快夺权,那就必然会被政治清洗。
“现在的世界发展迅速。它不再像过去那样缓慢爬行,而是在奔跑前进”(1941年披汶演讲内容)
当前,我们面临着十字路口。一个方向是顺应我们的意愿蹒跚前进。在这个道路上,民众将不会被搅扰……但是,国家会因为我们无法跟上其他国家的前进步伐而走向失败。另一个方向则能够确保我们的国家摆脱所有危机,并能在当前和未来引领我们不断进步。
我同意社会运动将我描绘为‘领袖’,因为我希望其他人相信我们的全体国民能将信任赋予‘领袖’一人。领袖因其丰功伟绩而必将为人民所追随。
我们缺乏有凝聚力的核心。我们拥有的是民族、宗教、国王以及宪法。但是,民族尚未真正成形,宗教己失去信徒的尊崇,国王仅能在相片上看到的孩子,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。国家正面临缺乏凝聚力核心的艰难时刻。因此,我要求你们追随总理。(1942年内阁讲话)
在西方民主国家,组织内阁是通过选举议员进入议会,而不是依靠军人与警察的武力。
政府并不是驱逐或歧视其他人,而是希望泰国-泰人所拥有的唯一土地的经济活动能真正体现公平。
对于我们国家而言,除了团结一致、携手奋进之外别无选择。
如果华人要分成两个集团,泰国不会干涉,因为这是华人内部事务。但是,如果华人忘记自己居住在泰国并且互相争斗,泰国将非常失望。
国民党造成了太多的麻烦,他们贩卖鸦片,并使泰国在联合国被指责。
当战争结束时,世上将不会有小国,都将会合并成更大的国家,因此我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:要么变成一个大国,要么被另一个大国吞并。
一个强大的军队对于防范外国入侵和镇压君主复辟是必要的。
既然泰国的华人不能到台湾去,也不能到红色中国去,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困难,因此,他们应该得到谅解的对待、泰国人民的同情以及政府“一切可能的帮助”。
旨在提升民族精神和道德准则,并把进步的趋向和‘新鲜感’灌输到泰国人的生活中。
一切为了我们的泰人兄弟。
我们不能要求立即获得武器的援助,我们要有尊严地行事。
泰国不应超过一个小国所能实现的目标,政府应把外交政策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。
现政府及我本人所主要关注的是,如何为国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比其他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。
国民“脏乱差”的传统陋习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,甚至影响到要求法国归还领土的谈判,法国人大可堂皇表示:国民粗鄙若此,何敢妄言收回领土。不如将领土留法国治下,尚能保持整洁卫生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