裴松之有哪些作为与成就-在政治与史学方面 (裴松之的主要著作)
裴松之,372年~451年,,字世期,河东郡闻喜县人,东晋、刘宋时期官员、史学家,为,三国志注,的作者,与其子裴骃、曾孙裴子野,史学三裴,之称,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,一起来看看吧,裴松...
裴松之(372年~451年),字世期,河东郡闻喜县人,东晋到刘宋时期的官员兼史学家。他最出名的活儿就是给《三国志》作注,和他儿子裴骃、曾孙裴子野并称“史学三裴”。
裴松之出身河东裴氏,那可是世代公卿的顶级士族。他八岁就能把《论语》《毛诗》背得滚瓜烂熟,妥妥的神童。初仕东晋,当过殿中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这些官,后来还做过故鄣县令、尚书祠部郎。刘宋代晋后,他也没闲着,零陵内史、国子博士、中书侍郎一路升上来,最后封了西乡侯。元嘉四年(427年)他当南琅琊太守时退休,结果朝廷又把他拽回来,先做中散大夫,后来升太中大夫。元嘉二十八年(451年)去世,活了八十岁,在当时可是高寿。
他在政治和史学上都挺有能耐的。
义熙初年(405年),裴松之当尚书祠部郎,管祭祀这摊事。那时候东汉末年传下来的毛病还在——人死了爱搞石室、石兽、碑铭这些,而且越搞越奢靡,东晋这风气更盛,官僚地主家私立碑铭成风,净写些夸自家功绩、标榜门第的假话。裴松之看着就来气,直接上书朝廷,说这玩意儿得管!他说碑铭是留给后人的,得跟实际情况相符,不然真假难辨,后人信啥?他建议得让大伙儿公议认可了才能立碑。朝廷还真听了,从此禁绝私立碑碑,多少刹住了这股歪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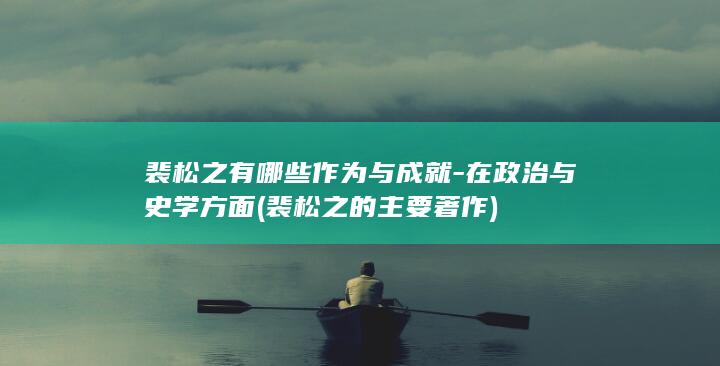
要说裴松之最牛的,还得是给《三国志》作注。这活儿是宋文帝亲自吩咐的,让他把《三国志》里的史实充实起来。裴松之干这活儿可认真了,不光实地考察遗址、听老人回忆,还把地名、人物、事件一条条翻书考证。
他在给皇帝的表里说,自己的注分四类:补阙、备异、惩妄、论辩。补阙就是补陈寿漏记的事,备异是存录不同的说法,这两类最多;惩妄是驳明显的错,论辩是评论史事或书,这两类少但重要,常带“臣松之案”“臣松之以为”。
补阙的例子多了去了。曹操搞屯田这大事,陈寿就写了五十来字,裴松之补了一百多字,说明这政策多关键;诸葛亮七擒孟获,陈寿一笔带过,裴松之补了二百多字,讲这“攻心为上”的门道;王弼搞玄学,陈寿就二十三字,裴松之引了好几本书,把他的生平、学说都补上了;还有马钧那个发明狂,陈寿压根没提,裴松之补了一千多字,指南车、翻车、连弩这些发明全靠他的注才传下来。连曹操的《明志令》、李密的《陈情表》这些重要文献,都是靠裴注留到现在的。
遇到一件事,不同书记载不一样,裴松之就全抄下来(备异),再判断哪个靠谱(惩妄)。比如刘备三顾茅庐,《魏略》和《九州春秋》说诸葛亮先找刘备,裴松之把两说法都记上,又搬出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“先帝三顾臣于草庐”,证明肯定是刘备找诸葛亮,不是反过来。还有甄皇后的事,王沈《魏书》把她夸得天花乱坠,裴松之直接说这书“崇饰虚文”,陈寿不收这部分,确实有道理。要是陈寿错了,他也不包庇,比如《吴书》里楼玄自杀的事,他引《江表传》说“这个说法更合理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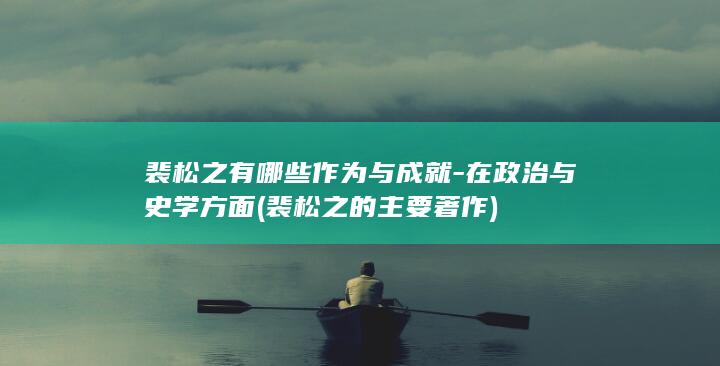
论辨就是他发表看法,评史事、评史书。评史书时,他挺在意体例,比如陈寿把贾诩(搞谋略的)跟荀彧荀攸(德智双全的)放一传里,裴松之说这“失其类”,应该跟程昱、郭嘉这种谋士合传。叙事上,他强调通顺,还注重人物外貌描写,比如觉得陈寿没写荀彧长相可惜,特地引书补充,说这样史书才好看。
历史评价
当时的人对他评价很高,宋武帝刘裕说他“廊庙之才”,《宋书》夸他“博览坟籍,立身简素”。后来《四库全书》总目提要说他注《三国志》网罗的书多,很多失传的六朝旧籍还能靠他的注看到,虽然有点爱博爱奇显得杂,但考证的人离不了他。明代胡应麟更直接,说他是“史之忠臣,古之益友”,这话挺中肯的。唐代刘知几呢,一方面说他“以广承祚所遗”,一方面又嫌他“不加刊定,恣其击难,坐长烦芜”,看来也是又爱又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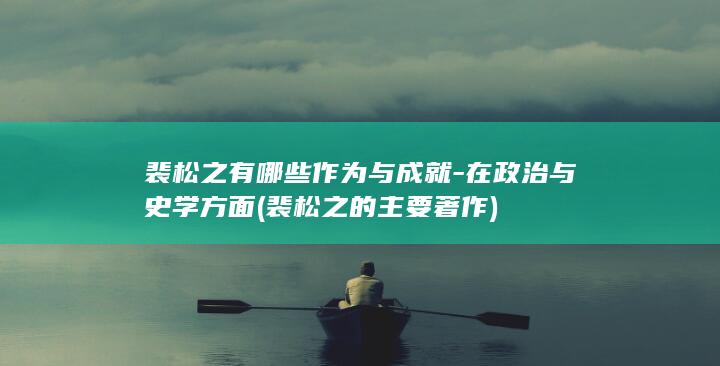
清朝的钱大昭说裴松之“引据博洽,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,别成畦町”,侯康也夸他“裴《注》尤博赡可观”,看来后世对他的史学功底是服气的。
宋武帝刘裕:裴松之廊庙之才。
《宋书》:博览坟籍,立身简素。
唐代史学家刘知几:①次有好事之子,思广异闻,而才短力微,不能自达,庶凭骥尾,千里绝群,遂乃掇众史之异辞,补前书之所阙。若裴松之《三国志》。 ②少期集注《国志》,以广承祚所遗,而喜聚异同,不加刊定,恣其击难,坐长烦芜。观其书成表献,自此蜜蜂兼采,但甘苦不分,难以味同萍实者矣。
南宋藏书家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·卷四》: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,鸠集传记,增广异闻。大抵本书固率略,而注又繁芜。
明代学者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卷十三》:裴松之注《三国》也,刘孝标之注《世说》也,偏记杂谈,旁收博采,迨今借以传焉。非直有功二氏,亦大有造诸家乎 ! 若其综核精严,缴驳平允,允哉史之忠臣,古之益友也。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:①宋元嘉中,裴松之受诏为注,所注杂引诸书,亦时下己意。综其大致约有六端:一曰引诸家之论,以辨是非;一曰参诸书之说,以核讹异;一曰传所有之事,详其委曲;一曰传所无之事,补其阙佚;一曰传所有之人,详其生平;一曰传所无之人,附以同类。其中往往嗜奇爱博,颇伤芜杂。如《袁绍传》中之胡母班,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,乃注曰“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,事在《搜神记》,语多不载”,斯已赘矣。《钟繇传》中乃引陆氏《异林》一条,载繇与鬼妇狎昵事; 《蒋济传》 中引《列异传》 一条,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,迎孙阿为泰山令事; 此类凿空语怪,几十余处,悉与本事无关,而深于史法有碍,殊为瑕颓。②然网罗繁富,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,尚一一见其厓略。又多首尾完具,不似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皆剪裁割裂之文。故考证之家,取材不竭,转相引据者,反多於陈寿本书焉。
清朝学者钱大昭《三国志辨疑》:①世期引据博洽,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,别成畦町。②裴氏注摭罗缺佚,尤为功臣。
清代史学家侯康《三国志补注续·自叙》:陈承祚《三国志》,世称良史,裴《注》尤博赡可观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