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秘-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不如汉唐吗 (“明朝”)
明朝万历年间,退休回家的明朝内阁大学士于慎行,在其著作,谷山笔麈,里,写下了自己的重要疑惑,都说唐朝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,可唐朝皇帝单是给郭子仪赐宴,就花了十多万两白银,中晚唐的藩镇犒赏兵士,更动辄上砸...
明朝万历年间,退休的内阁大学士于慎行,在《谷山笔麈》里写了个大疑惑:都说唐朝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,可皇帝给郭子仪赐宴,一出手就是十多万两白银;中晚唐的藩镇犒赏兵士,动不动就砸百万两;再看汉武帝讨伐外敌,几十万人规模,看着都烧钱。
可再看看“我大明”呢?于慎行估计都得叹气:别说平时动兵调粮,就说万历朝鲜那场仗,不过派了四万人过去,为了军粮军费,恨不得把国库掏空,勒紧裤腰带都凑不齐。这天上地下般的对比,那简直是“古今物力,何以相悬若此”——怎么“我大明”,还没汉朝唐朝有钱呢?
其实于慎行发这感慨的时候,还是明王朝财政比较稳定的“万历中兴”时代。后来再看十七世纪上半叶,风雨飘摇的明王朝,穷到缺粮缺饷最后上吊,就知道于慎行这声叹息,哪是什么痛苦领悟,简直是句虐心的神预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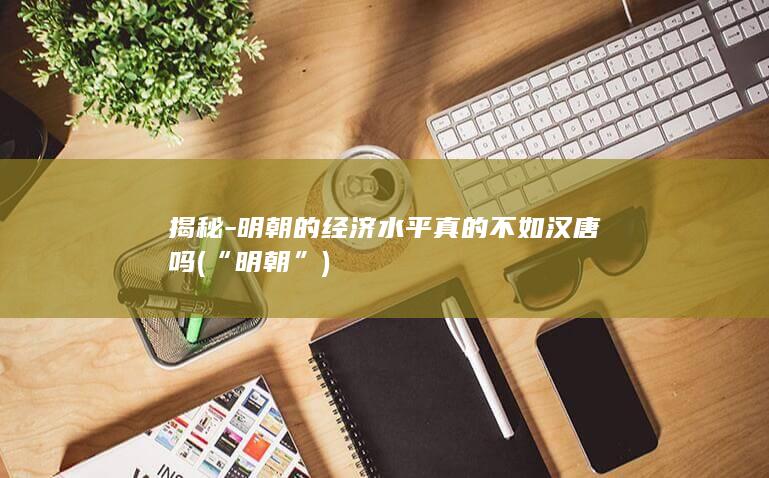
那明朝的经济水平,真像于慎行疑惑的那样“不如汉唐”吗?其实吧,北宋的社会经济水平,早就把唐朝甩好几条街了。而明朝洪武二十六年时的耕地面积,达到了八百五十万顷,比两宋最高值还多三百万顷,税粮收入更突破了三千二百万石,是宋元两朝最高数值的一倍多。
到了于慎行当“阁老”的万历年间,明初那点“产值”简直不值一提:《明实录》里说,天顺年间山西阳城一地的铁产量,顶明初洪武年山西全省七倍。于慎行自己也在《谷山笔麈》里吐槽,北京城里卖酱油的小贩,看着一身朴素沿街叫卖,其实是“有千万之资”——说白了,就是“土豪满街走”。
这个年代,也是明王朝奢靡风气疯长的年代。卖酱油的“千万之资”算啥?利玛窦笔下的明朝官僚,饮宴吃通宵是常事,每顿都是新奇食材堆满桌。《五杂俎》里的明代市集,年节时人挤人,各种宝货看得人眼花,“人烟凑集……总四方土产奇珍”。士大夫们的生活更是讲究,官员家女眷戴的珠冠,造价动不动就千两白银。年轻的读书人也以奢靡为荣,昂贵的湖罗衫在他们中间风靡,啧啧。
所以说,不管是社会经济水平,还是城市商品经济,于慎行年代的大明朝,甩开汉唐真不是一星半点。可为啥偏偏是不争气的大明国库,落到“不如汉唐有钱”的窘境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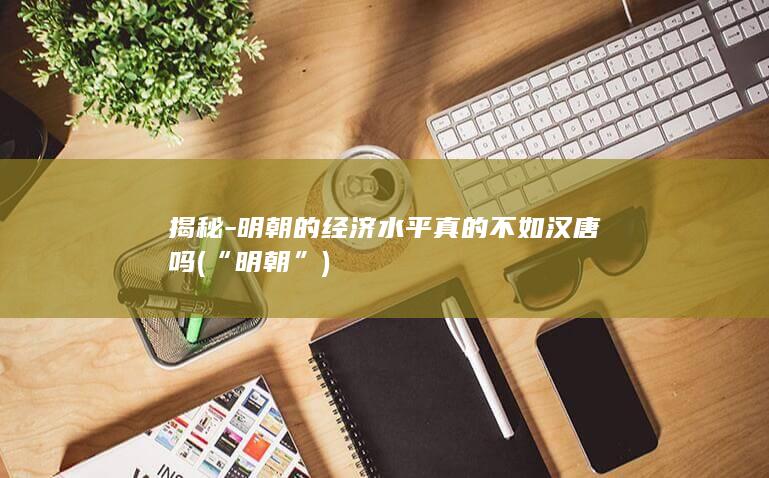
是因为明朝收的税太少吗?万历皇帝眼皮子底下的卢沟桥,四十里路,老百姓得交“炭税”“煤税”“草税”,然后“桥有税”“口有税”“门有税”。走这么一小段路,就是“重叠如之”——说白了,就是层层扒皮,每一步都要钱。
这套“层层扒皮”的操作,普通百姓哪受得了。卖酱油的“千万之资”是有的,但那只是个别行业。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朱赓就叹气,说更多的京城商户,“十室九空”,受不了盘剥的都跑了,剩下的也是“犹满路哀告”,日子苦得要命。
跟明朝农民比起来,这苦还算不上啥。明朝农民的赋税,说是“税轻”,但明王朝惯用套路就是“加派”。不止明末“加派”辽饷,比如“养活藩王”这事儿,“加派”是常操作。单是陕西白水县,万历年间每年为养当地藩王,就加派白银七百五十两。万历年间“赐瑞王田”“福王就藩”这些家务事,也全靠“加派”买单。《白水县志》里形容:具系宗室日繁,剜肉医疮——说白了,就是大明朝多一个藩王,甚至藩王家多生个娃,苦农民就得被剜一次肉。参考明末宗室几何级数的增长,晚明农民到底被割了多少刀,想想都心疼。而且这“割”出来的钱,没几个铜板进国库。
当然,要说大明“税轻”,最心知肚明的还是于慎行他们士大夫阶层。明初制度,士大夫没多少特权,地方官也就减免部分赋税劳役,该扛的一点不能少。可一代代大明官员精准钻空子,到了万历三十八年,士大夫们享受的赋税劳役“优免”数额,比张居正改革时暴涨了十倍。这“优免”出来的钱粮,当然甩锅到苦农民头上。
所以就有了《西园闻见录》里的咄咄怪事:“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,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”——有钱人一分钱税不交,穷农民什么钱都得交。交不起?只能举家逃亡。逃都没地逃,反抗的烈火自然说烧就烧。至于大明的国库?自然也就跟着“烧”没了钱。
比起于慎行大惑不解的“古今物力,何以相悬若此”,后来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,倒用账单写了答案。《后鉴录》里统计,李自成从北京拷掠的七千万两白银里,“侯家什三,阉人什四,官什二”——大明朝的钱,都跑到这群蛀虫家去了?
这声发问,对着那“账单”,除了叹息,剩下多少深思,谁品谁知道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