背后什么原因-为什么说唐德宗很像崇祯皇帝 (背后什么原因引起的)
每当我看到唐德宗上位时的操作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明朝的崇祯皇帝,他们上台之后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,把把火都烧得大快人心,比如说,他们一上台,都是严厉打压宦官集团,但是结果呢,他们都是很快栽了大跟头,下面...
每当我看到唐德宗上位时的操作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明朝的崇祯皇帝:他们上台之后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,把把火都烧得大快人心。
比如他们一上台,都先拿宦官集团开刀,下手那叫一个狠,看着大快人心。结果呢?没过多久,俩人都栽了大跟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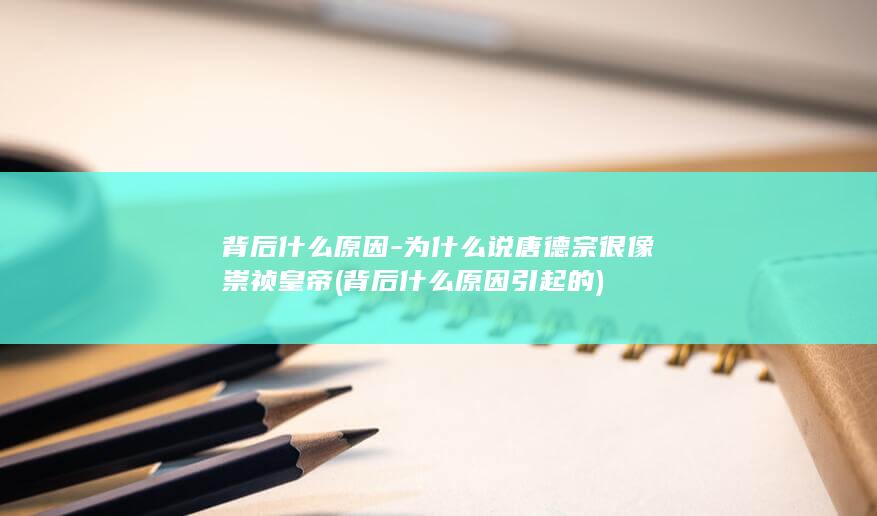
崇祯搞了一堆“教科书高度认可”的操作后,敌人直接打到了帝国都城下面。
然后呢?崇祯皇帝又开始信宦官了!官员们一看,急得直跳脚:“您怎么能这样啊?”
崇祯的态度就一句话:“别忽悠我了。我打压宦官的结果是啥?整个帝国好像没人管了!你们让我不信任宦官,行啊,你们自己争点气啊!问题是,你们一个个看着都像王八蛋,我能不信任宦官?”
唐德宗也差不多,搞完“教科书操作”,直接逃出了长安城。
然后呢?唐德宗也回头信宦官了。这回官员们连嘴都懒得张了——谁让打压宦官那会儿,皇帝差点连枪杆子和命都没了呢?
你现在还敢劝皇帝压制宦官?皇帝就算不好当面反驳你,明天找个机会收拾你,肯定不带犹豫的。
代宗那会儿,皇帝就差没拿着喇叭喊了:“宦官们,出去办事,能收红包就收红包,别客气!”
史料里写:“代宗优宠宦官,奉使四方者,不禁其求取。尝遣中使赐妃族,还,问所得颇少,代宗不说,以为轻我命;妃惧,遽以私物偿之。由是使公求赂遗,无所忌惮。宰相尝贮钱于阖中,每赐一物,宣一旨,无徒还者;出使所历州县,移文取货,与赋税同,皆重载而归。”
用高大上的理论看,这肯定是“国家要完”的标志——皇帝咋还纵容、鼓励宦官收红包呢?但从权力的小九九看,这明显是在给宦官系统“充值”啊!
各军政长官愿意给宦官塞红包,无非就俩原因:一是怕宦官在皇帝面前说坏话,二是盼着宦官在皇帝面前说好话。
只要他们有这心思,在争权夺利时就得抢着讨好宦官。这样一来,皇帝就能把人事权力慢慢收回来。
说白了,一个人想当官,一门心思讨好宦官,皇帝决定谁上的时候,就有底气了——谁敢反对?那个给宦官塞了大红包的,第一个不干啊!毕竟这官位是靠“红包投资”换来的,要是黄了,不是白花了?
关键是,当官能不能成,居然要看宦官脸色,那大家不得更使劲讨好宦官?越讨好,皇帝的权力就越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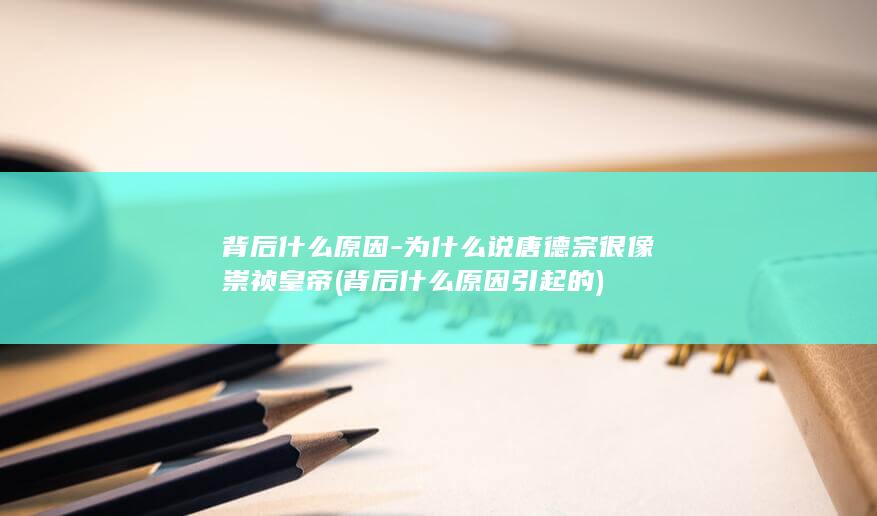
但靠这法子加强皇权,皇帝其实特被动。
当个官还得靠讨好宦官,这叫什么事?还得塞红包,这更叫什么事?
后来,各大军区反皇帝时,一个重要理由就是:“我们这些将领,全是靠给宦官塞红包才当上的!关键是,我们还借了高利贷给宦官塞红包!这种将领当了大帅,能不贪污腐败吗?”
史料里写:“自大历以来,节度使多出禁军,其禁军大将资高者,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,以赂中尉,动逾亿万,然后得之,未尝由执政;至镇,则重敛以偿所负。”
唐德宗按教科书操作时,还干了一件事:砍了中央政府的一部分“隐性收入”。
好多时候,皇帝、皇后过生日、过节,或者官员到中央报到,地方大佬都得“孝敬”银子。谁给得多,皇帝就对谁好。
更逗的是,有的皇帝还拉地方大佬打麻将——当然,规矩你懂的:只能输,不能赢;输少了,皇帝还不高兴!
史料里写:“上末年尤贪财利,刺史、二千石罢还,必限使献奉,又以蒲戏取之,要令罄尽乃止。”
看皇帝这么玩,用大道理说,吃相太难看了。其实啊,这就是皇帝变着法儿让藩镇交税。中央税不够,地方又不愿意直接交,那就换个词:过年过节给“礼”,总行了吧?
这钱进了皇帝的“小金库”,其实还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。中央和地方一直在抢税源,中央要是没本事征税,就只能跟地方“大包干”:每年交多少银子,剩下的归你。
地方势力一大,一听“税”字就头大——这不等于中央要插手我地盘吗?所以皇帝只能换说法:“我是皇帝,你是地方官,过年过节给我送点礼,总该吧?我过生日、我老婆过生日、我儿子满月结婚,你总该表示表示吧!”
看皇帝天天唱“今年过节不收礼,收礼只收XXX”,确实觉得皇帝想钱想疯了。拉着你打麻将,输个百八十万不让下桌,更是疯得不轻!
但你要是真琢磨琢磨,就不是这回事了。
比如崇祯皇帝过生日,也玩这套,官员再哭穷,不得掏点钱?皇帝倒倒手,拿这笔钱花在政府开销上,多少能解点财政饥渴啊。
说到宫廷库房,很多人觉得这是皇帝用来腐败的。其实这些钱还是中央财政,只是直接捏在皇帝手里。
安史之后的大唐,藩镇经常得拿银子孝敬皇帝。皇帝生日、元旦、端午、冬至,都得献礼。
史料里写:“代宗之世,每元日、冬至、端午、生日,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,贡献多者则悦之。”
史书肯定骂这种行为——用大道理看,皇帝贪财贪到没边了。其实呢,地方藩镇反中央时,总说:“我们不想压榨老百姓,实在是不压榨就没钱孝敬皇帝!只有我们割据,才能阻止皇帝逼我们压榨老百姓!”
所以唐德宗上位后,就不能再逼地方大佬过年、过节、过生日时“孝敬”银子了。
史料里写:“癸丑,上生日,四方贡献皆不受。”
教科书上的操作,永远是大道理,把现实的利益争夺给抹平了。可真到玩权力的时候,皇帝都信“闷声发大财”——有些事不能拿到台面上,但你不这么玩,就玩不转。
最典型的就是让宦官抓军权、财权、人事权。放教科书里,这绝对是错题。问题是晚唐皇帝都这么玩,偶尔想拒绝,栽了跟头后,变本加厉接着玩。
宦官、朝臣、军人都是人,很难说谁正义谁邪恶。但在舆论战里,宦官永远是被黑的“反派”。皇帝信任重用宦官,这叫什么事呢?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