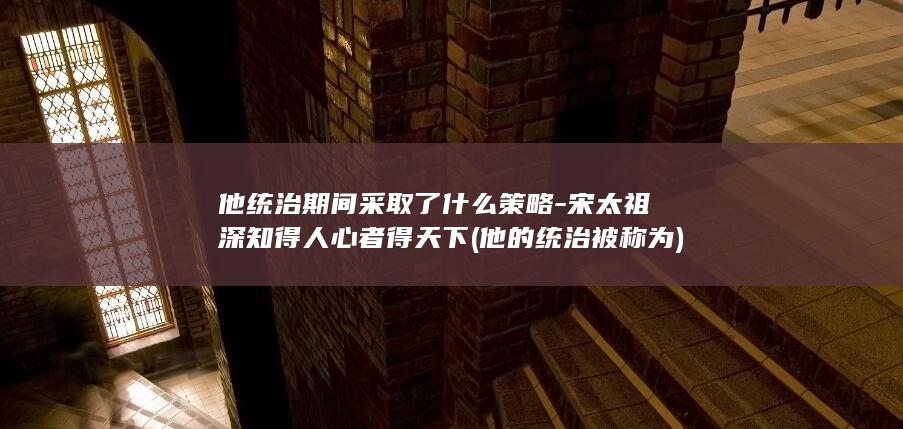他统治期间采取了什么策略-宋太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 (他的统治被称为)
作为开国君主,宋太祖在统一大局巳定的情况下也没有志满意得、忘乎所以,平定南方诸国后,各国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,宋太祖将它们作为战备物资,全部收贮在内库,从不随意挥霍,宋太祖本人有射猎和職衡,踢...
宋太祖这人吧,当了开国皇帝,天下眼看要统一了,也没飘。平了南方各国后,那些国家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运到东京,他全当战备物资收在内库,从不乱花。他喜欢射猎和踢球,刚当皇帝那会儿,手痒了就拉几个手下玩。
有天他在后苑射鸟呢,大臣跑来说有急事求见。太祖接过奏章一看,不是啥马上要办的,火了,训了大臣几句。那大臣还挺犟,说“奏章的事是不急,可总比射鸟急吧”。太祖更气了,抄起玉斧就扔,撞掉人家两颗门牙。大臣没吭声,跪地上把牙捡起来揣怀里。
太祖问“你想拿这个告我?”那人说“不敢!但您是天子,一言一行史官都记着呢。”太祖一听愣住了,对啊,当天下主,说话做事都得注意,赶紧把人扶起来道歉。后来啊,他慢慢就把射猎和踢球的瘾戒了。
宋太祖懂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,统治时用“布声教”的策略,说白了就是恩威并用。他挺会笼络人。陈桥兵变后,他刚进皇宫,见个宫女抱着周世宗的儿子,问赵普、潘美咋办。赵普说“斩草除根”,潘美低头不吭声。太祖说“夺了人家皇位还杀人家儿子,我下不了手。”潘美这才说“我以前也在世宗手下,劝您杀,对不起世宗;不劝,您又说我忠心不够。”太祖摆摆手“你带回家当侄子养吧。”
有次国宴,周世宗留下的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,在席上吵吵,还跑到皇帝屏风前大哭。有人劝他,他不管。太祖没生气,让人扶他出去。大臣说“前朝遗臣在宫里哭,是想念世宗,得罚。”太祖不以为然“他就是个书生,我知道啥人,别提了。”王著酒醒了后怕,见没被杀,从此死心塌地跟太祖。
作为武将,赵匡胤知道纵兵掠民会惹反,所以打仗总嘱咐士兵别滥杀。平后蜀时,王全斌在城里杀了不少人,还让士兵抢东西,百姓反了,太祖罚了他。曹彬围金陵时,太祖三番五次传旨“别伤城里人”,金陵百姓保住了命和财产。消息传到朝廷,群臣祝贺,太祖反倒哭了“百姓受割据苦,我安抚他们,可攻城肯定还有人死,我心里难受。”
他对少数民族也用“布声教”。党项的李彝兴想和宋交好,送了300匹好马。太祖很重视,让人做条玉带回赐。他特意问使者“李彝兴腰围多少?”使者说“腰腹很大。”太祖笑“看来你们元帅是个福人啊。”让人做了条“大得像合抱的树”的玉带。使者带回去,李彝兴感动得不行,后来打北汉时真帮了宋军大忙。
为了边境安宁,他对少数民族“悉心绥抚”,不听话的大臣,不管功劳多大,都撤。灵武节度使冯继老抢羌人的羊马,惹骚乱,太祖免了他,换段思恭。段思恭按太祖意思安抚羌人,边境安了,太祖还赏了他不少东西。
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消除藩镇乱象,太祖搞了不少改革。杯酒释兵权只是开始,后来又推了三招:一是建枢密院,管调兵但不带兵;三衙带兵但没调兵权,军权分开了,皇权好控制。二是“内外相维”,军队分两半,一半在京城,一半在外地,京城人多,外地合起来能抗衡京城,谁也乱不了。三是“兵将分离”,用“更戍法”,士兵经常换地方,兵不识将,将不识兵,将领没法拉帮结派。
削藩镇用“强干弱枝”:一是削权,把节度使兼的州郡划成中央直属,派文官当地方官,不听节度使的。对老盘踞的节度使,也用“杯酒释兵权”罢免了。二是制钱谷,设转运使,地方财赋除了日常开销,全交中央。三是收精兵,各州把骁勇的士兵送到京城当禁军,地方只剩老弱,没法跟中央抗衡。
削弱相权也狠。宰相以前坐着奏事,有天早朝,太祖说“我眼花,你们把奏疏拿过来”,等范质、王溥站起来,侍卫悄悄把凳子搬走了,之后宰相就得站着奏事。不光这样,军权给了枢密院,财权给了三司使,宰相就管点民政。
他还搞“官、职分离”,设参知政事、枢密副使、三司副使当副手,互相牵制。宋代“官”是品级,领工资;“职”是荣誉,没实权;只有皇帝“差遣”的临时职务才有实权。这样谁也没法把权、名、威望集一身,权大的可能职低,职高的可能没权。
为了扩大统治基础,他改科举,范围放宽,不管贫富,有文化都能考,还防舞弊。他重文轻武,刚即位就修孔庙、开儒馆,请名儒。针对五代学校荒废,他拨款修国子监,开学还送酒祝贺。他认为“乱世用武,治世用文”,后来文人越来越多,慢慢取代武将在政治上活跃。
他搞的这些改革,加强了中央集权,给后世经济文化发展打了好底子,成了宋室“祖宗家法”。不过这些防弊的法子也有毛病:杯酒释兵权让兵将不熟,打仗不行;官机构重叠,互相扯皮,人越来越多,事越来越慢,到北宋中后期,国家就积贫积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