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都喜欢旅行吗-为什么宋朝的文人总是在旅途中 (他们都喜欢旅游用英语怎么说)
宋代有许多旅行诗,宋朝文人多在旅途中,山头云似雪,陌上树如人,,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多么清雅的审美空间,京口瓜洲,一水之间,王安石孤舟独渡,得到的是江南岸边好大的一片春色,那一个生机盎然的,绿,字,染透了...
宋代文人好像特爱在路上晃悠,写了不少旅行诗。“山头云似雪,陌上树如人”,读着就让人觉得,那会儿的人审美可真清雅。京口瓜洲,一水之隔。王安石孤舟过江,一抬眼就撞见江南春色,那个“绿”字用得绝,整个宋诗的调子都让这绿染透了。
人在旅途,哪有停的时候。诗人晁冲之有首《夜行》写的就是这个:“老去功名意转疏,独骑瘦马取长途。孤村到晓犹灯火,知有人家夜读书。”上了年纪的晁冲之,独自骑着瘦马赶路,天快亮时到了个孤零零的村子,见一户人家的窗户还亮着灯,心里一暖:谁家读书人这么拼啊!他原本也是读书人,考过试,得过功名,可朝廷里党争厉害,他和几个兄弟没少受罪,如今心灰意冷,只想躲山里当隐士,想想真让人叹气。长途跋涉人困马乏,风里来雨里去,世态炎凉都看在眼里,他却偏偏记下这孤村夜读的一幕,心里头全是羡慕那耕读的日子,也藏着点自己不想再出头的郁闷。景和情揉一块,真叫人读着心里发紧。
比晁冲之混得强些的陆游,照样对世道人心感慨万千,去临安上任时心里憋着一肚子火。要不是那两句诗太亮眼,谁还记得他这趟差事?《临安春雨初霁》里写:“世味年来薄似纱,谁令骑马客京华?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矮纸斜行闲作草,晴窗细乳戏分茶。素衣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。”你看他住客栈,雨下了一宿没停,沙沙打在瓦上、树上,第二天一早,杏花开了,有人提着篮子走长街叫卖。这景儿是挺美,可一想到大宋当时内忧外患,他心里就堵得慌。“一夜雨”“明朝卖”,听着像因果,其实“明朝卖”是虚写,飘着呢。好多注家没品出这两句的深意,陆游那是得了“政治病”啊!他天天盼着朝廷来场“一夜雨”,可这“雨”是啥,他没说透,但里头肯定有话。所以不能光当风景看,看他旅店里那闲得发慌的样子就懂了。
“矮纸斜行闲作草,晴窗细乳戏分茶。”他就在废纸上瞎写写字,一遍遍沏茶,看那茶沫子细白如乳,看得都入神了。日子惬意是惬意,可也太单调了,温馨里透着呆板,忧愁怎么也挥不去。诗人那股子沉稳、忧郁,还有在安静里的坚持,对未来的懵懂,全在这两句里了。
还是旅行,梅尧臣回老家宣城东溪,写了首《东溪》,记下“野凫眠岸有闲意,老树着花无丑枝”这千古一景。诗曰:“行到东溪看水时,坐临孤屿发船迟。野凫眠岸有闲意,老树着花无丑枝。短短蒲耳齐似剪,平平沙石净于筛。情虽不厌住不得,薄暮归来车马疲。”
野鸭在岸边打盹,半睡不醒,闲得不得了;一丛丛老树临着水,枝头新花开得精神,一点不显老。这跟刘禹锡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简直绝配,一个味儿。
这首诗得从诗美学里说道说道。一般说梅树,曲的才美;盆景,残的、病的才好。你想啊,老树开新花,比新枝吐翠好看多了;要是野鸭嘎嘎叫,哪配得上溪水哗哗流?梅尧臣挑这景,可贵的不只是眼力,是他怎么看景——这景里头藏着他自己的审美。了解他的都知道,这审美、这诗美学,跟他走南闯北的经历、对家乡田园的喜欢,还有越来越想归隐的心分不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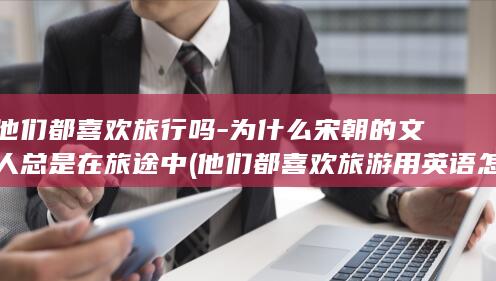
宋人把诗像撒绸缎似的铺在路上,把那些大道理、愁思都丢在山水里。问一句:宋人爱跑路,今人就不爱出门?再问:宋人爱写路上见闻感想,今人就只会傻看景,不吭声?才不是!
今人活得可欢实了,撒欢打闹比宋人厉害多了,“到此一游”的诗篇堆成山,比唐宋加起来还多。可这些诗里有啥金句?景怎么选的?审美有啥新发现?道理讲明白了吗?说实话,少得可怜,千人一个样,万口一个调。就算抄别人的,或者生搬硬套,也让人看不懂,还美其名曰“朦胧”。
那为啥今人和宋人差这么多?有两点跑不了:江山不是宋时的江山了,人心也没从前静了。咋说?你还能看见开花的古树吗?就算乡下,老树不死也被锯了,侥幸活着的,也被绑到哪个大城市当盆景。绿油油的天然草芽也难找,就算有,上面还被人剪成简体字或英文字母。山顶上像雪球似的云,看不到了;陌上“像人一样站着的树”,也想象不出;更少有“万壑有声含晚籁”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的体验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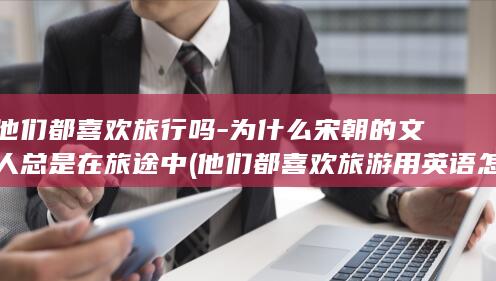
更要紧的是,人心浮躁,环境又糟,心都麻木了,“灵”没了。看不到读书人的窗灯,看不到半睡半醒的野鸭,看不到江南的新绿,倒也罢了。可那份宁静,那份坚守,甚至该为家国、为众生留的忧患之心,都丢在宋朝的河边、卖杏花的巷子,或是芦花荡深处了。唉!

